民俗于电影并不陌生,以罗伯特·费拉厄迪的《北方的纳努克》为首的民族志电影以及此后出现的人类电影、民俗学电影,都具有较强的 民俗情节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,传统民俗在第五代、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频频“抛头露面”,国内掀起了一股“新民俗电影”浪潮,民俗与电影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却重大的转变。《红高粱》中的“颠轿”、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中的“点灯”“捶脚”等题材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骚动,随之而来的是对电影与民俗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层反思。

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

《红高粱》
《菊豆》被张艺谋搬上银幕后,获得多项国际性的大奖。1990年连获第九届香港金像奖十大华语电影之一,法国第四十三届戛纳电影节路易斯·步努埃尔特别奖,西班牙第三十五届瓦雅多里德国电影节金穗奖,以及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的金雨果奖。这些特别的“光环”无以说明了电影《菊豆》是一部内容丰富很有研究价值的作品。自从电影《菊豆》在获得如此殊荣之后,人们都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解读。有的人说这是中国俄狄浦斯情节的表现。有的说这是对中国封建势力的控诉。本文要说的不是它的内含,抽空了它的内容把整个作品“外壳”置于读者面前来,让读者看到导演的中国风格。整个故事在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染坊里,演绎着“他们”的悲欢。《菊豆》是一篇具有浓厚民俗意蕴的电影作品,“民俗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,同时它是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。”《菊豆》把意蕴丰厚的民俗景观作为故事的背景,将电影的人物和事件安置在民俗语境的叙述框架之内。
民俗元素的运用增加了影片的深度,内涵更丰富,象征意味更加明显,对问题的揭示更加深刻。《菊豆》中,天青和菊豆乱伦,一个是渴望性和爱的满足,过真正男人的生活;一个是对杨金山的仇恨与厌恶,同时也夹杂了性得不到满足的苦闷,继而在对方那儿寻找真正生理和感情上的藴籍。虽然两人的苟合有一定的合理性,但毕竟是丑陋的,为社会所不齿。于是,天青和菊豆尽管在家里虐待朱老汉,但在村人面前却不断伪装,从不敢撕下脸皮。这也是因为道德约束深入人心,没有人敢违背。(这种道德上的自律也有民俗的成分,民俗包括道德风尚。)在杨金山葬礼上,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,两人对死者虽带着怨恨,却也不得不做按照规矩和传统送他最后一程。葬礼越是隆重,他们受到的心理身体折磨也越严重。漫天飘洒的纸钱,喧天的唢呐,沉闷的土铳、大红漆的上好棺木,无处不是对徽州丧葬风俗的浓墨重彩的渲染。村人散后,天青菊豆茫然地趴在地上站不起来,像是死了一样,他们灵魂也受到了一次拷打。如果没有对葬礼这个民俗元素重点刻画运用,影片的讽刺效果也会减轻,这种人前人后的巨大反差也会相应缩小,影片对主题揭露的深度会降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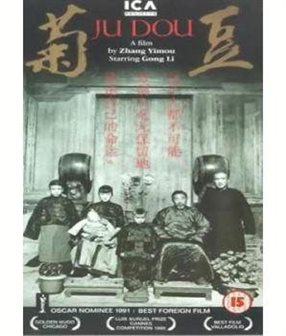
在民俗与电影这场美丽的邂逅中,究竟暗藏着多少机遇,又有多少风险?民俗给电影增添了无上风光,电影又将把民俗带到何处去?这取决于电影、民俗、传播等领域的诸多要素,值得学界更多的关注。
欢迎打赏
